黄达: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与领航者
2018-10-25 青野鸿蒙
在中国金融学领域,无论在校学子还是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一个名字:黄达。
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是高端决策者不可或缺的智库。作为第一批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他在中国金融教育乃至财经教育领域所作的贡献令人仰止——新中国成立后每一次金融教材的编写,都有黄达的辛勤耕耘。
黄达,1925年2月22日出生,天津市人。
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首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致力银行货币、金融学研究60年,对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有人称他为:“中国货币理论研究及开拓者”、“中国金融学奠基人”,但自诩为“土法上马”、自学成才,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货币金融研究的黄达更看重自己教书育人的成就,“要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学生,讲授先进的货币银行学”,是他最大的愿望。

成长经历
黄达1925年2月22日出生于天津。祖上是安徽凤阳人,曾随朱元璋起义、燕王“靖难”,叙战功,调天津左卫指挥使佥事,予世袭,自此著籍天津,曾有显赫的官家地位。到清代,黄家失去了官身背景,于是“世业儒”,逐渐成为天津的普通市民。
黄达的祖父黄文是清末民初典型的本土知识分子。“光绪甲午入郡庠,戊申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毕业,宣统元年奖给举人中书科中书,中华民国二年北京大学校法科毕业”。黄达回忆,他十岁时翻祖母的一个大躺箱,见到过祖父的“毕业文凭”,文凭上方印着两条大龙,比一开整张的纸还大,是用大竹筒装着的。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文凭上各门课的考试成绩:大多数课程的考分不及格,而语文却是90多分。
黄达的祖父极其重视对子侄的教育,传统文化底子深,但也不保守。他将黄达父辈的四个子侄都送进洋学堂读书。黄达的父亲黄树人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工学院的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到现在河北省南部的峰峰煤矿当工程师。

黄达自认有个温暖的家庭、幸福的童年。“有的是比较自然的行为约束,而并非举手投足处处受到严格管束;对孩子没有时时高调说教的精神压力,好像更相信孩子可以自我养成做一个好人的人生目标。”黄达说:“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市民家庭呢?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传统但并不保守,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更敬守中华的习俗。在这样的家庭中我是幸福的。和谐温暖,难于养成棱角特别分明、易于追求极端的思维模式;无恒产,则形成了人生之路应是凭本领自食其力的理念。自食其力主要是指读书识字,反映了‘世业儒’家世,也就是中国历史里‘士’的精神传承。”
1932年,黄达暑假插班进入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二年级。当时,这个小学在天津颇有名气。这年黄达七岁半,父亲已经教了他小学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本。初小的课程主要是语文、算术、常识课。黄达都能专注学习,除了刚插班的第一个学期外,从二年级第二学期到四年级的第二学期,学期考试的成绩他都是全班第一名。
上小学高年级后,黄达拿钥匙打开母亲的箱子,他发现其中的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都是父亲的文具、纸张、书籍,还有一卷工程画。开始,母亲不让翻,怕他弄坏了,后来慢慢也就不禁止了,但每次都要反复嘱咐他要收拾好。那一卷工程画,黄达每次都要一张一张地看。其中有一张使他学会了用圆规和直尺画五边形;有的使他初步懂得如何画投影。工整的工程字字体,对他后来书写拉丁字母和数字颇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卷工程画使他对将来要当工程师的梦想有了具体的形象寄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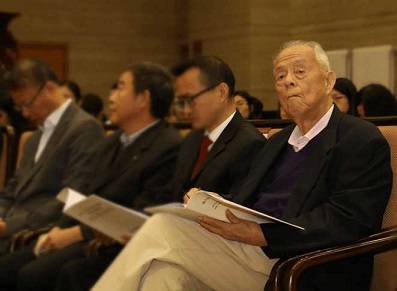
1937年,黄达小学毕业,“七七事变”爆发,天津街面立即笼罩着人心惶惶的气氛。就在这样的气氛下,黄达的大姐还带他从租借地赶到南开中学参加了升学考试。但不久,日本轰炸并占领了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南迁大后方。上南开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30日,天津沦陷,成为日本占领区。“逃反”到租借地的黄达进入私立志达中学。学校坐落在英租借马场道,学校董事会的头头是一位下野的军阀,这个学校虽然不知名,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却有个不错的教师班子。“在志达中学我读了初中一二年级。学习收获是什么,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考试成绩也不好。”黄达说。
在这两年,黄达的英语学得很糟糕,二年级的暑假,父亲让他上新学书院的暑假补习班,准备让他转学。新学书院的背景是海关,特别重视英语,毕业后可到海关谋职。但是,由于父亲的去世,黄达转学新学书院的事无从提起了,就是志达中学的学业也中止了。在暑假尾,父亲去世了,祖母也随之去世了。失去了经济来源,全家决定从生活费高的英国租借地搬回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地”。在这样的变故中,1939年的下半年,黄达处于失学状态。
1940年,虽然家境窘困,但黄达的叔父还是让他尽快恢复了学业,在汇文中学,黄达插班重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1940年暑假,志达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找到黄达,说要考“铃铛阁中学”,即当时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的高中,并约黄达一起去考。这是天津很有名的中学,本想试一试,不报多大希望的行动,没想到竟然考取了。于是高中三年,黄达得以就读天津这所最古老的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浓郁——教授黄达的,有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裴学海和数学家杨学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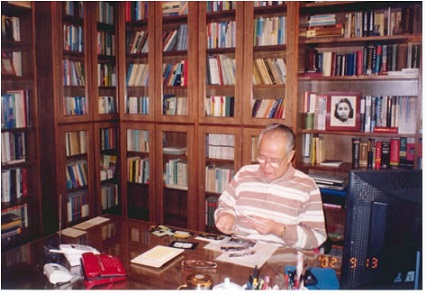
黄达少时志向既不是当教师,更没想到研究经济学,他一心想学工,像爸爸一样当一名工程师。但高中毕业之际的一场伤寒病,使他失去了升学的机会。病愈后,为了糊口他做过旧政府机关的小职员、在一家私人照相馆当过帮工,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使他认识到现实社会的艰难。1946年春,21岁的黄达满怀憧憬,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想追寻一种崭新的生活。适逢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地区招生,他顺利地考取并进入联大政治学院财经系,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参加土改运动。不久,学校从张家口撤退,转到冀中平原,这期间,黄达转为该校政治学院研究生,研究“边政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这年岁末,黄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黄达分配到校部从事行政工作,并再次参加土改运动,先后任华北大学班主任、区队助理。当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际,分配黄达从事经济理论教学,此时,他终于放弃了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接受了关乎终身职业的人生安排——自1950年黄达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金融教研室工作起,他便开始了对货币银行问题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干,就是60多年。

专注教学
黄达的大部分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了教学研究上,即使在改革开放不久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以后,也没有中断过教学工作,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必须遵守的准则。
与很多“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黄达自称“只留下四本教材”——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80年代中期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21世纪初的《金融学》。
改革开放后,在教材编写上,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已经有很好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没有必要编写中国自己的教材。黄达却坚持,在中国的讲坛上,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货币银行学,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他认为,翻译的教材,是外国的教授以外国的背景写的,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学生,如果只用外国课本,就会出现学生学在本乡本土,却不了解国情的现象。因此,他始终坚持尊重自己的积累,并以自己的领会和理解为主,在尽力借鉴吸收西方知名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同时,力求讲明白中国金融领域的实际。

黄达编写的第一本统编教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由于封面为蓝底色,学生都叫它“蓝皮书”,阐述了货币流通与信用的基本理论与业务知识。1981年,黄达编写了《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问题》,这本书也因封面底色而被称为“黄皮书”。书中结合社会主义实践对计划经济中的货币、资金、财政、金融关系进行了阐述。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西方货币金融学”课程,介绍货币供求及其宏观均衡理论,但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仍占主体,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多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分而论之。这一年黄达出版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是一本使黄达深负盛名的理论专著。书中对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相继出现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信贷规模急速扩张和信用膨胀、财政收支从节余转向赤字、建设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扩大等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把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平衡、信贷收支、财政收支放到这个统一的大框架中进行宏观分析,深刻揭示了信贷收支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财政信贷统一平衡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个分析框架虽然是就计划经济体制搭建的,但从货币角度分析宏观经济运行,则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适用性。该书获得了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对很长一段时间的行政决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货币银行学教材普遍分两块,一块是西方的货币银行学原理,也有称作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另一块是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也有叫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前者主要从批判的角度来阐述原理;后者则在“黄皮书”基础上讲述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金融问题。这种“两张皮”的格局,对金融理论研究和教学都造成相当大的困惑。1992年,黄达“将两个思路之长汇集为一个体系”,出版了《货币银行学》,这本教材集改革开放最初十几年金融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成果之大成,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本教材的内容扩展至货币金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理论体系、知识结构,还是篇章布局、行文表述都堪称典范。它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至目前仍在广泛使用的最权威的教科书,使数十万学子受益,并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数项荣誉。
2004年,黄达主编的《金融学》出版,这是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中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这本书是黄达花费数年心血研究界定的宽口径“金融”为范畴,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同步,充分吸收国内外金融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立足中国实际搭建的金融学科基础理论框架。这个新的框架取西方金融与中国金融之精华,融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于一体,以逻辑和历史的线索交织金融原理与实践发展,以现代货币创造机制联结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以原理阐释和问题讨论贯通理论金融与应用金融,精巧地架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学科理论殿堂,代表了同期中国金融学科基础理论教学的最高水平。

学术思想
“立足本土、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严谨治学”,这是《黄达书集》出版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对黄达治学精神的概括。她评价黄达教授的学术思想,“对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形成和建设,对财政金融理论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黄达的货币金融思想发展到第二个阶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破坏,这时出现的种种问题,无论是马列经典著作还是苏联经济理论,都找不出答案。此时,黄达开始直面现实,从原先的以教学为主转向以研究为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认真严谨地进行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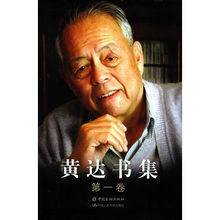
十年动乱,黄达没能逃脱挨批判、写检查、关牛棚的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达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货币金融思想的发展日臻成熟,学术成就也开始开花结果。作为货币金融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黄达很早就开始对物价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1979年春,黄达在一次讨论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问题的高级别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论文《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这篇文章的观点,有的学者赞成,有的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乃至酿成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物价和通货膨胀问题的一场讨论。黄达的论点是,多年来,我国各种商品的生产条件、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各商品的价格却长期不变,其比价也很不合理。要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而调整比价往往会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他提出,对于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应该区分短期和长期来理解。作为短期的物价方针,在调整不合理比价时,要尽可能控制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不使相邻年度之间有跳跃性波动;作为长期的物价方针,则可理解为允许物价水平时而调高、时而持平的交替过程中小幅度提高。他认为,采取这样的方针绝不等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出物价逐渐上涨的趋势。这种物价上涨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历经坎坷,当时黄达提出的物价改革观点颇为超前,“鼓吹”通货膨胀的先河,一下子难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改革开放后,黄达坚持立足中国的现实研究经济问题,接连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解的作品,对财政金融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系统探讨。

2010黄达出版了《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黄达说,“以此为结点,由于年事这个不可抗拒的原因,我对于货币银行学、对于金融学科,已经有好几年未能进一步思考了。”不过,在黄达的一篇名为《货币银行学到金融学》的演讲中,他说:“金融天地,浩渺幽深,览胜揭秘,乐何如之”。黄达60年的货币银行学教学研究生涯,同时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金融问题探讨研究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脉络。从这个角度看,黄达的学术经历,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