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绝唱《广陵散》·中国音乐故事
2018-3-3 青野丰隆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它是中国汉族古代一首大型琴曲,中国音乐史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著名十大古琴曲之一。近代琴学家杨时百,在其所编《琴学丛书》的《琴镜》中就认为此曲源于河间杂曲《聂政刺韩王曲》。

“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标题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首大型器乐作品,它萌芽于秦、汉时期,其名称记载最早见于魏应璩《与刘孔才书》:“听广陵之清散”。到魏、晋时期它已逐渐成形定稿。随后曾一度流失,后人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发现它,谱中有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1段、小序3段、大序5段、正声18段、乱声10段、后序八段六个部分。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琴曲的内容据说是讲述战国时期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

在《广陵散》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写的就是这个故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为父报仇的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或许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的这种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嵇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并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倍受人们关注。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十三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嵇康要比阮籍更高出一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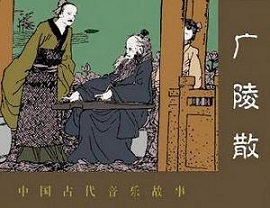
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广陵散》乐曲中的反抗精神引起笑傲山林的嵇康的共鸣,他把对恶贯满盈的路人皆知的司马昭的痛恨全都凝聚在乐曲中。司马昭很想利用嵇康的才华`名望为自己服务,多次要他出来做官,嵇康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的好友山巨源因劝过他出来做官而收到嵇康的绝交信。司马昭对嵇康的拒绝自然怀恨在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岂不妙哉。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但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接纳。而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他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乐曲一开始,仿佛是若有所感所思,有种推敲和辨认的等待,沉稳、倏然,音色悠扬清澈、不着尘污。但是仅略做迟疑,音色陡然下落,情绪随即一层层推开,虽然节奏依然有条不紊,但揉弦时毫无迟疑,充满了决断和帷幄。行至乐曲中段,音调突然上扬,并很快将此乐句做以反复,似用来强调语气,仿佛一石击开千层浪,一种凛然的霸气、一束清矍的孤傲,跃然而出。曲中的顿音似是斩钉截铁之念已捻熟于胸。随着乐曲的推进,琴声变得萧瑟、激昂,带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气势。到高潮时,琴弦弹拨得密不透风、节奏急促、气氛紧张,音律振荡之间有种遮掩不住的兵戈戎马之气,流露出一派昂扬不屈的气节。像烈酒盈杯后一饮而尽的飒爽,像洒酒于足下方寸之地以敬鬼神的悲切和决然。勾、挑、揉、打、抹等手法的变化,揉在琴声中,令乐曲有了万般变化着的丰富音色和跌宕起伏的气韵,让人目不暇接,神魄随之飞扬。那些铿锵的音符,仿佛是从琴弦上飞溅而出,夹杂着力量和激情喷涌迸发,一泻千里,有种掷在耳中都感疼痛的结实。

可以想象嵇康临刑时弹奏《广陵散》时的酣畅和沉浸。高士之所以高,最在气节。那种从容,尽释满怀的抱负,将生死掷于身后的铮铮铁骨,面对一生的感慨,唯有指下寥寥数根琴弦,代舒情怀。能解《广陵散》的词句,莫过与嵇康自己的诗作:“凌高远盻。俯仰咨嗟。怨彼幽絷。室迩路遐。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姝颜。谁与发华。仰讯高云。俯托轻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 (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据说嵇康有一把名贵的古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佩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缩丝制成,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有一次,其友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胁,才使此琴免遭大祸。可以想知嵇康是将琴与性命等同相看。不过以嵇康之清高,不会为物所束,只是琴亦有魂魄,好琴亦为性命相惜的知音。此琴与嵇康共喜共忧、同歌同叹,相与相伴,琴与抚琴者相知相通,此种气血之交融,非言语能表述。所以嵇康才有临刑抚琴唤《广陵散》,其间的激愤、嗟叹与凄然,让人动容。

临死前,嵇康俱不伤感,唯叹惋:"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特殊的时代造就当时艺术的气质,我一直认为只有在特定的环境里,艺术才能做得原汁原味,换了个时间地点,只能想象,只能尽力去贴近以求抵达精髓,而永远无法企及原貌。所以嵇康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后叹曰:此曲“于今绝矣”,指的也并非是曲谱失传,而是指弹此曲其人其心其志,再难有同此情此境者!疾风方蹴就劲草之狂,此为《广陵散》之高绝也。

《广陵散》后来在清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但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