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镜堂:八旬建筑师遇上“云设计”
2020-7-11 青野丰隆
2020-07-11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何镜堂,1938年生于广东东莞,是获奖最多的中国建筑师之一,也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19年获评“最美奋斗者”。他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建筑设计师,设计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如今他根据疫情提出新的设计理念。

“好看的直线不一定要像尺子那样笔直,你细看,它有戏的。”不少建筑设计师常随身带着纸笔,一有灵感就拿出来画房屋结构,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设计师何镜堂就是如此。他两只手能平均使劲儿,右手把脑中构思描出来的同时,左手做笔记。82岁的他已经画了60多年的直线,设计出许多知名建筑。比如在广州山林间的白云山公园,置身其中仿佛“在花中走、云中游、山中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深圳科学馆、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等都展现时代特色。最近,何镜堂又站在了时代浪潮上,尝试“云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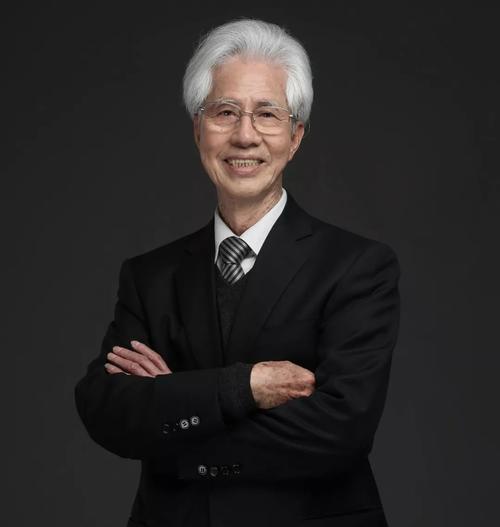
疫情也改变着建筑理念
在记者对何镜堂的视频采访中,他打开线上办公软件“瞩目”,将鼠标调成画笔,在共享屏幕上“画”了几条线,向记者介绍他设计的街道布局,“用这个(线上软件)能直接改图给学生看,告诉他们要修改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几个月,给各产业带来复工难题的同时,也加速数字化转型,许多人开始“云办公”。在建筑界,用软件做设计并不稀奇,但要根据多方需求不断修改方案,原本主要是面对面沟通,疫情则让更多设计师走上“云设计”。
何镜堂记得,疫情暴发后,许多正在盖的楼房被迫停工,他不必前往工地查看进度,“疫情是暂时的,设计仍可继续,疫情也让我们发现,搞设计的也能进行线上沟通,不一定要集中到一个地方才能办公。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很辛苦,我们虽不是医生,但把工程搞好也出了一份力。”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海南岛的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将进行改造,请何镜堂任总设计师。疫情期间,他不能去海南岛,但通过视频开会,解决了会址改造的难题。“视频、语音会议最大优点是能随时随地开会,而且一接通就能马上讨论,效率高。”如今,他手头上有二三十个工程,从去年9月至今签下的工程合同额度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其中大部分来自最近一个季度的新项目。
疫情也改变了建筑和空间的设计思路。疫情早期,一些楼房的管道排气系统不佳、导流差,病例排出的病毒经由排气扇传到其他户,导致病毒传播。这早有先例。何镜堂记得,非典期间,香港淘大花园内的卫生间排水口下防臭U形聚水器的水干涸,排气不佳,一名病例腹泻,粪便携带的病毒通过厕所的管道系统在大厦内传播,导致300多人感染。因此,这次疫情暴发后,何镜堂在设计房屋时特别注重通风系统,“设计高层建筑时要特别注意管道排污,还有通风排气,比如和空调师傅反复沟通,确保空调管道的设计能挡住室外病菌”。
此外,设计城市公共空间时也不能“摊大饼”。“摊大饼”是较为常见的空间设计思路,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不断扩张,可是一旦发生传染病、地震等突发事件,可能影响救援进度。“以后设计公共空间时,要适当留空,楼层间最好有绿地隔开,还要提前想好哪些建筑适合改建成像方舱医院这种临时救援点。”在何镜堂看来,重要的还在于理念。“‘地球村’注重人和各物种的关系。人类建造房屋、改造城市,不能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要尊重它们,否则它们可能会报复的。”

“当时觉得自己重生了”
记者采访何镜堂是在他刚过完82岁生日后不久。这几年,每逢生日,学生都会准备生日蛋糕为他庆生,今年赶上疫情,他就在家里和妻子过。何镜堂在60岁才过了人生第一个生日,当时的生日蛋糕是“深圳科学馆”。
何镜堂的哥哥是广州美术学院第一届本科生,家门口是东江支流,小镜堂常跟着哥哥到江边写生,画乏了就踩水流,时而溯流而上,时而奔跑而下,与自然为伴。那时起,他萌发了对美的认知。
在东莞中学念书时,何镜堂听老师说:“建筑师既要懂艺术,又要懂技术,所以是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他便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何镜堂入学后,和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交流,“第一次知道了抽水马桶”,开始对现代都市生活感兴趣。何镜堂话不多,不爱出风头,为人低调老实,还好遇到了恩师夏昌世。
夏昌世毕业于德国蒂宾根大学艺术史研究院。当时,德国的建筑教育流行包豪斯学派,注重建筑的实用性,开创现代建筑设计教育体系。何镜堂常去夏昌世家画图,“夏老师叼着烟,偶尔过来瞧一眼,指导一下”。那时的建筑学教材有不少是国外的,全英文,到老师家要搭公交,他就将信纸裁成1厘米宽的纸条,写满英文单词,搭公交时就拿出来背。
夏昌世主持设计广西大学附属医院,让何镜堂设计门诊部。何镜堂常到医院观察人流路线,苦思“怎么通过布局防止不同科室交叉传染,又如何让焦急的病人和繁忙的医生快速穿行在不同房间”。他专门到北京查资料,在一家图书馆找到英文书《医院功能及设计研究》。那时没有复印机,借期只有3天,何镜堂就花了3天把整本抄下来,共16万个英文字母,工工整整,仿佛是打印出来的,抄本被何镜堂保存至今。后来,他的门诊部方案成了硕士论文《门诊部的候诊设计研究》。
刚毕业那会儿,何镜堂才27岁,意气风发,却几经辗转插队落户到湖北的偏远山区,之后又被调到北京建筑设计院。那几年,能看的书不多,他倒是花很多时间研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颇有收获。“时代越复杂,越要有直抵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就是要抓主要矛盾。每栋建筑的主要矛盾就是它要表达什么精神。”1983年,何镜堂终于得以践行这个心得。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大量基建项目重新开始,建筑界又活跃了。国家施行“研究生归队”的政策,何镜堂得以回母校华工工作。当时,深圳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准备盖些楼作为开会、招商、展览之用,比如位于市中心的深圳科学馆。科学馆举行设计竞赛,邀请华工建筑学院参加。校领导找到何镜堂,告诉他:“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要做一个外形突出且科技化的建筑,让人家一看就忘不了。”
接到任务时,45岁的何镜堂心想“机会来了!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马上思考模型,决定采用“母题重复”法。这是建筑学中常见的空间组织方法,就是用一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母题,用各种创意加以复制。他将“切西瓜”的动作放到建筑里,设计成八角形。八角平面可以灵活切割,内部空间大,而且各个角度都能吸收到光,采光很好。建筑外观的上中下均是八角形,很有现代感。模型做出来后的第二天,何镜堂就赶到深圳提交方案,当天下午便接到通知:中标了。
落成后的深圳科学馆包含500间会堂、200座学术报告厅等。“当时看着它,觉得自己重生了”。市民很快记住了它,称其“八角楼”。该馆和博物馆、体育馆等成为深圳八大重点文化项目,1989年获国家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后来还获评全国最优秀建筑创作大奖,带动了华工建筑学院的名气。请何镜堂设计建筑的人越来越多,他设计出许多经典建筑,于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还获得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在60岁的生日会上,学生给他准备了以深圳科学馆为模型的大蛋糕,重达25斤,几个人一起才抬到桌上。
如今,何镜堂在广州的工作室是几栋小平房,是他将80多年前的老院子改建而来的,房屋之间有小桥、流水,房间有落地窗,坐在里面能清晰地看到院子的行人和风景。何镜堂常和学生边吃边聊,正如40多年前,恩师夏昌世常带他到茶馆里边饮茶,边聊建筑。
“建筑是艺术,但又不像艺术品,一幅画要是画得不好,撕掉就完了。但房子是和住的人在一起的,盖好了就不能拆掉。你要尊重住在里边的人。”

何镜堂长期从事建筑设计、教学和研究工作,创立“两观三性”建筑论,坚持中国特色创作道路和产、学、研三结合发展模式,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作品。
他尤擅长文化、博览建筑和校园规划设计,主持设计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天津博物馆、映秀震中纪念地、钱学森纪念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和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等一批精品工程。

人物评价
何镜堂院士长期从事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哲理和创造思想,体现于大量的建筑创作作品中。(中国建筑学会评)
何院士“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建筑师中的一个,既完成了多样性建筑实践又通过理论分析来阐述实践, 其方式能真正地在与西方交流过程中产生共鸣”,他的“作品微妙而复杂,空间移动在限制与大胆之间穿梭,并没有刻板单一的设计模式”。(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斯科特•科恩、中国建筑学会评)
何镜堂主持完成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馆的设计恰恰是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很好转折点,是当代中国建筑的新语言”,“代表中国建筑的未来” 。(意大利著名建筑评论家卡萨帝(Cesare Maria Casat)、中国建筑学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