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40年•格非《褐色鸟群》
2021-11-10 青野龙吟
《褐色鸟群》是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格非。它是一篇闪耀着博尔赫斯式的诡谲与自我指涉色彩的典型小说。其新颖的创作手法,对心理梦境般的描写中,对人类自身竭力隐藏的本性也有着十分透彻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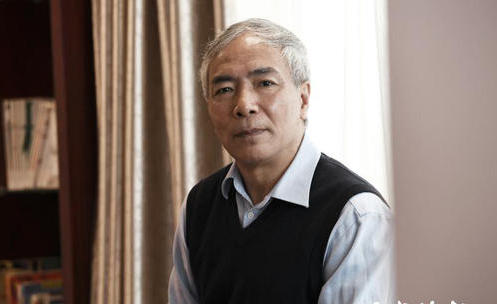
格非
格非原名刘勇,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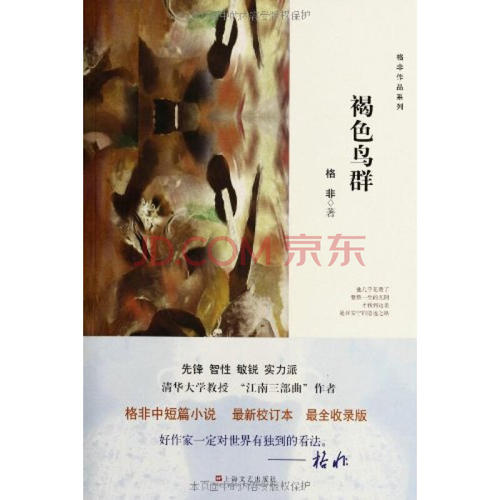
一说到《褐色鸟群》,很多读者心中应该会浮现诸如“难懂”、“深奥”或是“莫名其妙”之类的词语。作为一部先锋作品,《褐色鸟群》采用了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叙述,实验色彩非常浓重,甚至在先锋作品中也显得太先锋。我们可以将格非的处女座《追忆乌攸先生》归结为历史寓言,将《迷舟》理解成一种宿命传奇,却很难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描述《褐色鸟群》。他似乎是一个小说创作者对过往的回忆,又似乎仅仅是一个创作文本的过程……
主人公蛰居在一个叫做“水边”的地方,通过褐色鸟群的飞过隐约猜测时序的嬗递。这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无法分辨季节的变化”、“流星做匀速四周运动”和“鸟群会把时间带走”,诸如此类的描写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担心狗和人都要谋害他一样,当我们发现小说人物感知的世界出了问题之时,下意识想到的肯定是这个人出了问题。但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狂是为了揭示出“吃人的的社会”,而《褐色鸟群》中矛盾及非理性的叙述却难找到具体所指。
很多的读者之所以觉得《褐色鸟群》难懂,无非是难以理解它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文学作品一定要有其意义所指,一定要表达一些确切的东西,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但是一部小说能否仅仅是为了形式而存在呢?或者说一部小说是通过形式而非内容来表达?
作者格非曾介绍说《褐色鸟群》的核心结构得益于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朋友去买火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火柴盒,售货员吃惊地说,你有火柴为什么还要买?那朋友打开火柴盒,从里面拿出五分钱付给售货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结构,从火柴开始,到火柴结束。但是前后的火柴盒又有些不同,一个装着五分钱,另一个装着火柴。更有趣的是,装在火柴盒里的那五分钱,可以换来另一盒火柴。

这是一个盒子里套着盒子的故事,一环扣一环,最终回到原点。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在《褐色鸟群》中,棋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作者开头所说的那本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理解成我们所看到的《褐色鸟群》?小说的叙述方式并不是线性的,几个故事虽有关联但又不是完全符合逻辑——就像现实和梦境的关系,既有关联,也有背离。
“有一天,一个穿橙红(或者棕红色)衣服的女人到我“水边”的寓所里来……直到后来,她解开草绿的帆布,让我仔细端详那个夹子,我才知道果真是一个画夹,而不是镜子”,开头以现在时叙述我在“水边”遇见棋,我向棋讲述了追踪一个女人的故事,那个女人“她的栗树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曲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成沟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 ——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这是第一个故事。
“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滚在一起。他们沿着山坡往下滚,女人的茶绿色的头巾脱落在坡地上,她的长发飘散开粘满了草屑和泥土”,几年后我跟那个女人重逢了,但那女人却否认了和自己的相遇,并说自己从十岁起就没去过城里。从这开始发生的是第二个故事。
“她的衣服已被雨水淋得透湿。她披肩长发上不断地有一些晶亮的水滴滚落下来。她告诉我,她的男人死了”,女人跑来告诉我她的丈夫去世了,我和她结为夫妻,但她在结婚当天去世了,这是第三个故事。
“少女将那个帆布包裹搁在膝盖上,熟练地解开青绿色的带子。那是一面锃亮的镜子”,最后我又遇见了棋,但棋表示自己只不过是过路人,抱的并不是画而是镜子,甚至她根本不叫棋。这是第四个故事。
这几个故事组合在一起,给读者最直观地感受就是前后矛盾,不知道故事的真相。在《小说艺术面面观》中格非曾说:在个人与现实交错的空间结构中,我们通常生活在某种边缘地带,而不是局外;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看,情况更是如此,我感到现实是抽象的先验的,因而也是空洞的,而存在则包含了丰富的可能性,甚至包含了历史。这段话表明了格非前期的创作观,对我们理解《褐色鸟群》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事实上,对于生存于现实中的个体来说,回忆、想象等精神活动往往也不会是确切的。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非理性的幻觉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但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却把它们放在了中心位置。
或许《褐色鸟群》最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它讲了些什么,而是它是如何讲述的;或许《褐色鸟群》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之中,而在于它采取的方式之中;它为我们展现的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故事,而是存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小说核心意象“栗树色靴子”
读者感知
《褐色鸟群》注定是一篇你读过就难以忘却的小说,当然不止因为它不好懂。这部小说曾号称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但却很好看。
从最外在的方面说,《褐色鸟群》带给我的首先是语言上的快感。“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格非的语言从容而诗意,浸泡着丰富的回忆,勾起人的怀旧情绪。我的周围仿佛弥散升腾起茶色的烟雾,氤氲着歌谣湖畔的水汽。而当这样的语言与这篇小说里扑朔迷离的叙事相遇时,语言就显得格外神秘,扣人心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里的语言是诡异的,当故事还没有展开,当“我”还没有与“棋”相遇之时,语言已经为后面的叙事营造了绝好的氛围。对于一个看似没有逻辑的混乱的故事而言,也许,只有这样诗意而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才能拽着读者,陪文中的“我”走到故事的末尾。
而当我们进入到故事本身时,我们发现,世界在被格非一点点颠覆着。小说发表于1988年,而“我”讲述的1992年到“歌谣湖畔”再遇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回忆”,属于未来的时间。小说开头所写的“我”与“棋”的第一次相遇则是比1992年还要靠后的未来。小说的结尾,写到:“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这样时间漫延到了更加不可知的地方。我们的时间被颠覆了,回忆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交错在“我”与“棋”混乱的叙述里,混成一潭。而当故事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是前后两层的,不同的叙述视角在重复中交织着,以《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共同编织成一个故事。令人费解的是,所有我们前面已知的事实,到后面都会被颠覆,最终构成一串类似埃舍尔怪圈的系列圆圈。这一点评家们都有论及,郭宝亮将之比喻为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圆圈概括起来有三重:第一个圆圈,许多年前“我”蛰居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认识多年,我与她讲了一段我与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往事;小说的最后,“我”看到棋又来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二个圆圈,许多年前“我”从城里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来到郊外;许多年之后我又遇见那个女人,她说她从十岁起就没有进过城。第三个圆圈,“我”在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与女人和“我”讲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间构成相似与矛盾。这三个圆圈之间存在相互否定(矛盾)与肯定(相似)的多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这里,一切都难以确定。而故事的细微之处,前后矛盾就更多。比如“我”自称自己蛰居在“水边”,而棋则说“我”是住在“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我”跟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到断桥,看到她从桥上过去,而桥边“提马灯的老头”则否认女人从这桥上经过;更诡异的是,后来这个女人称当时在桥边的是她的丈夫;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丈夫淹死在粪池里,而“我”却看见棺材里男人的尸体似乎动了一下,而且真切地看见,那个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倘若我们可以《罗生门》中不同人的讲述归因于在一个罪案中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那么《褐色鸟群》中不同的叙述则显得荒诞得突兀——我们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动机,到小说的最后,都分不清黑白真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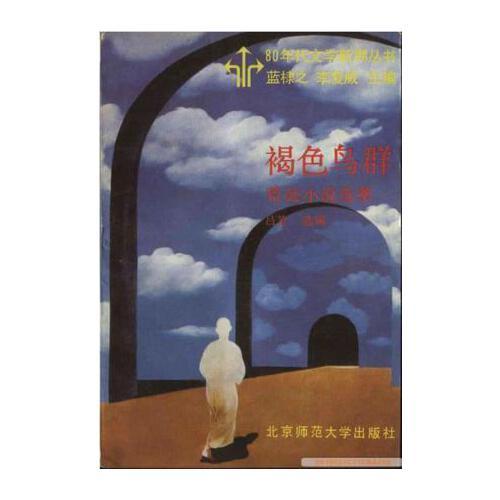
这样的叙事是完全符合先锋小说的特质的——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去找寻人物内心的奥秘和意识的流动。而格非的这篇小说尤甚。季红真先生认为《褐色鸟群》“由于过于抽象而丧失了叙事的本性,成为一种形式的哲学。”格非的确是在放纵着自己的文字,任它们在存在与虚无的混乱中冲击读者的意识,来完成自己的哲学思考,但是格非并没有忘记叙事的本性,只是《褐色鸟群》中的叙事,遵循了格非设定的哲学逻辑。格非明显受到了萨特等一拨人的影响。按照存在主义,所谓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规定性、个体性、结构性,都是人在与世界接触时主动存在的产物,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映,属于“自为存在”的性质,但这些都不属于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褐色鸟群》的叙事,就是在“自为存在”向“自在存在”的转换中,完成对存在与虚无的终极叩问。陈晓明论述得相当精辟:“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我认为,格非想要描绘的,是他眼中的存在与虚无混杂着的荒诞世间,而他将这世界的荒诞,浓缩在了一个关于“性、梦幻与感觉”这些人类最神秘领域的故事里。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都在质疑着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都在痛恨着这个世界的荒谬,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当我们在格非的故事中完全迷失了支配着的所谓“逻辑”月“定式”,迷失了时间与空间时,我们获得的也许是对这世界最真实的感悟,这就是阅读快感的由来吧,虽变态,但真实。